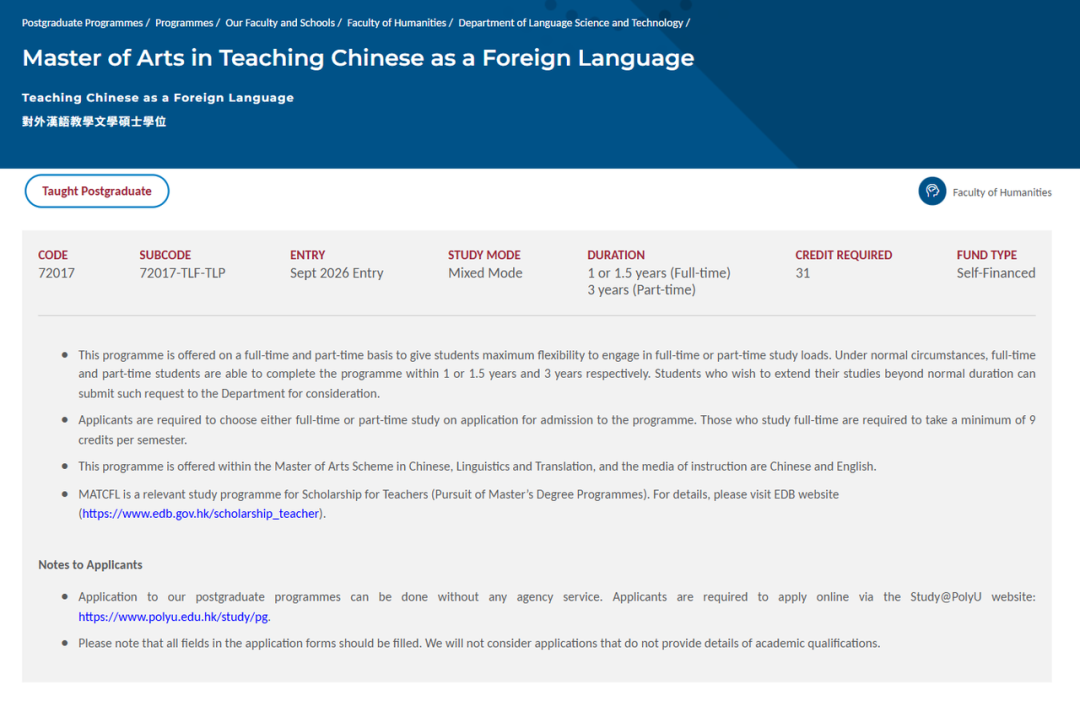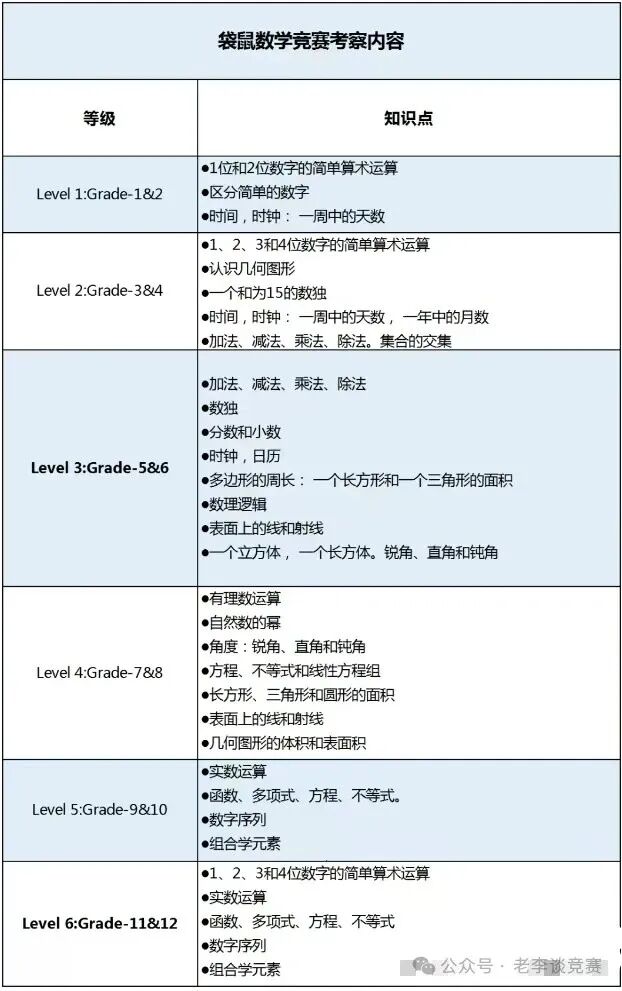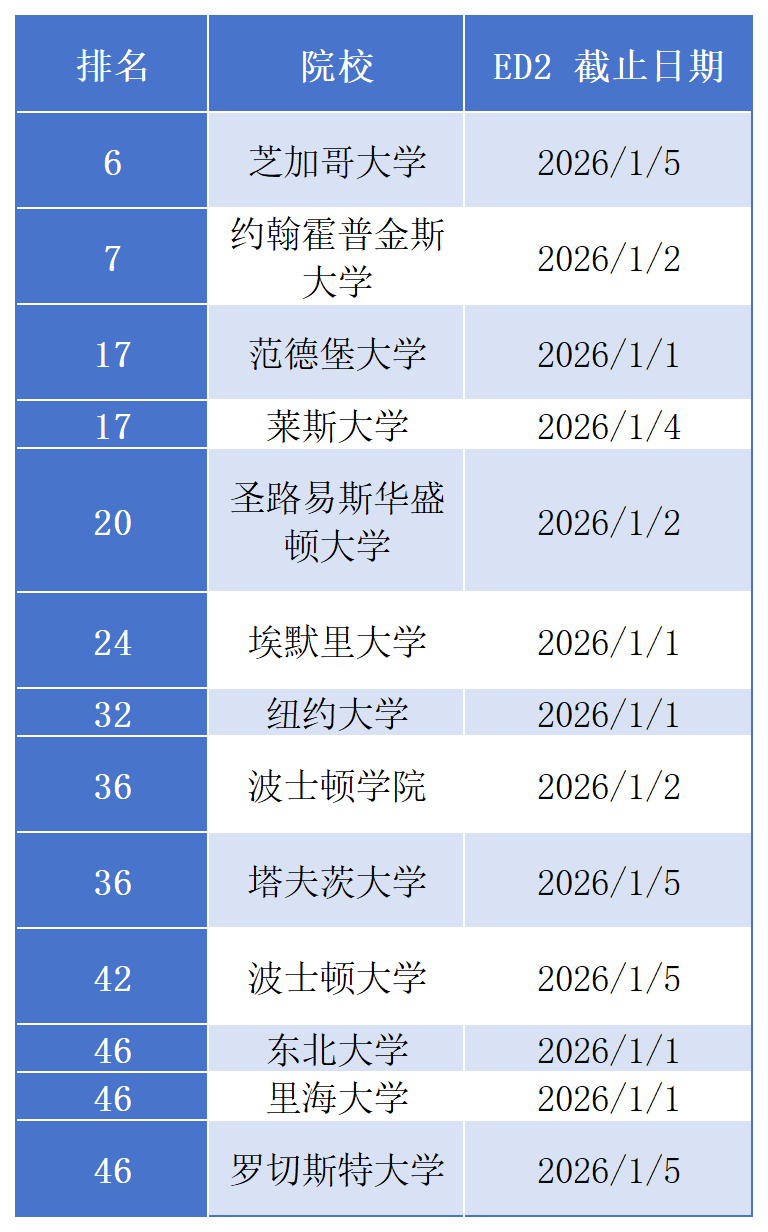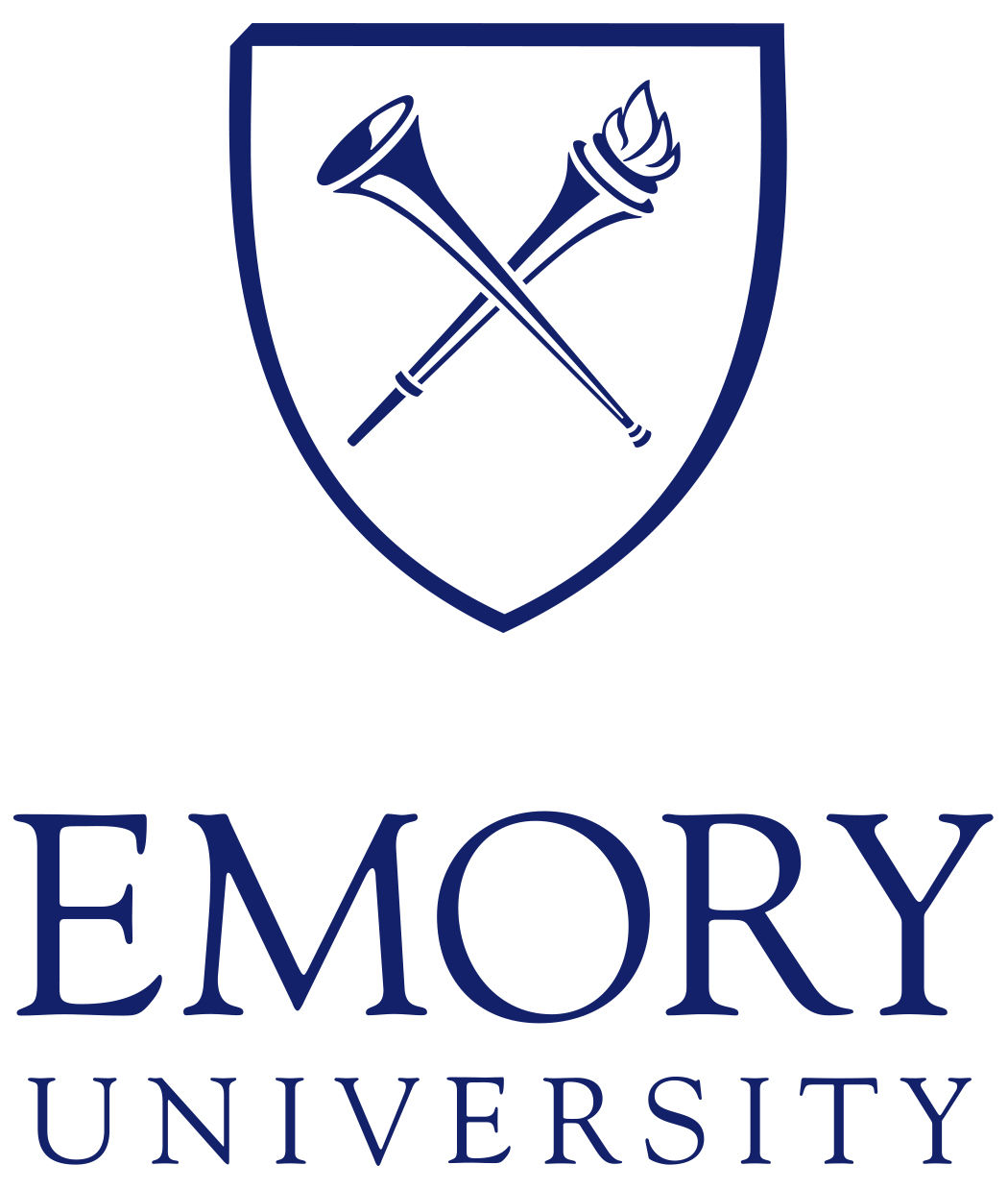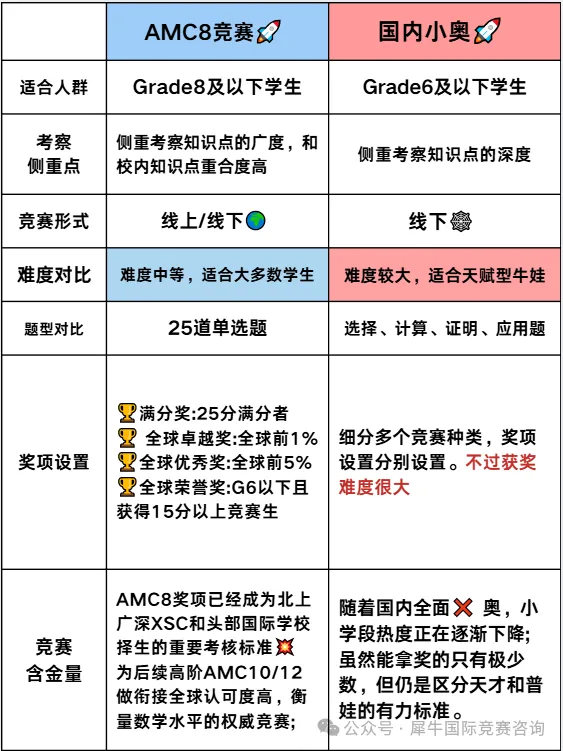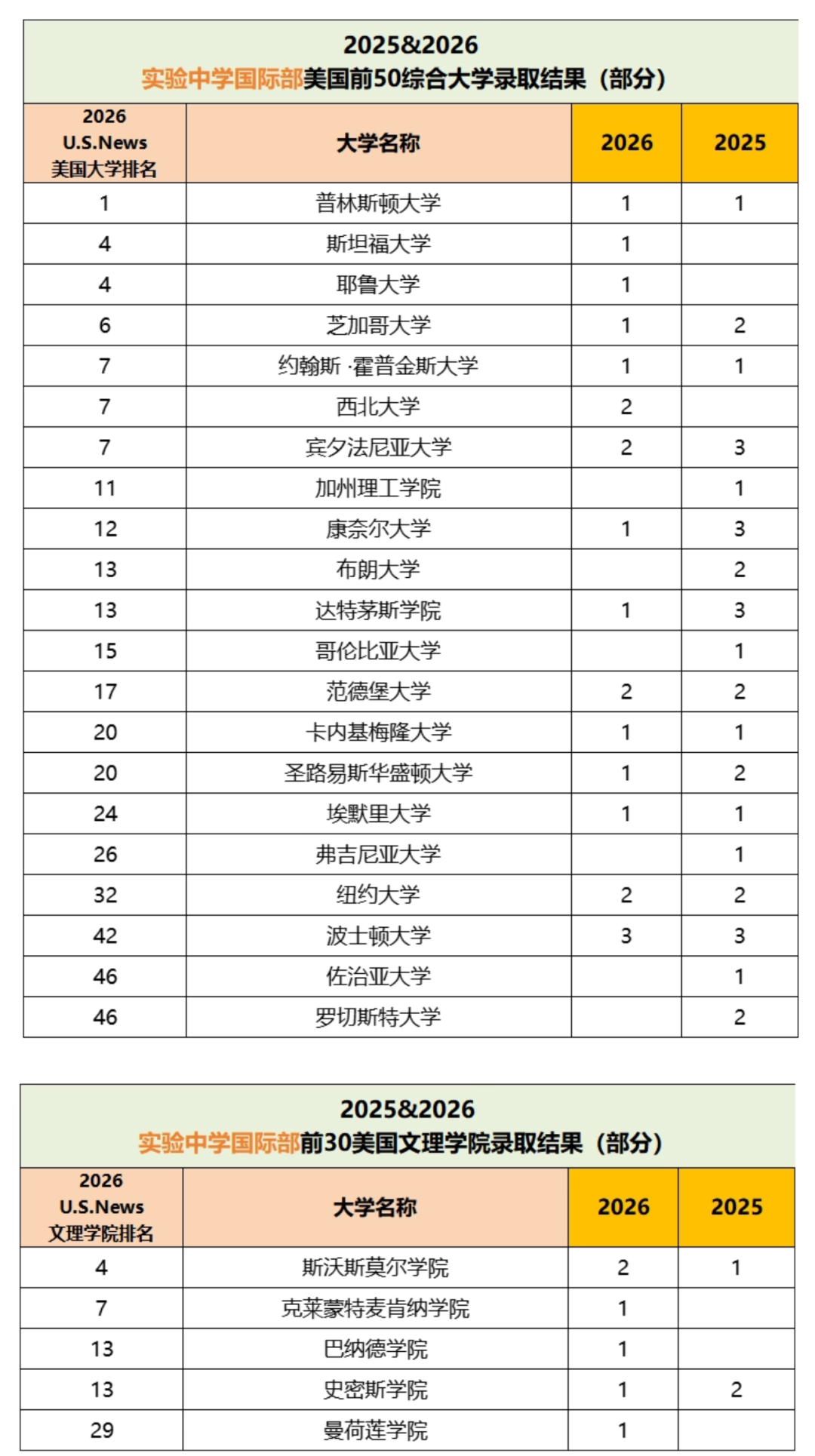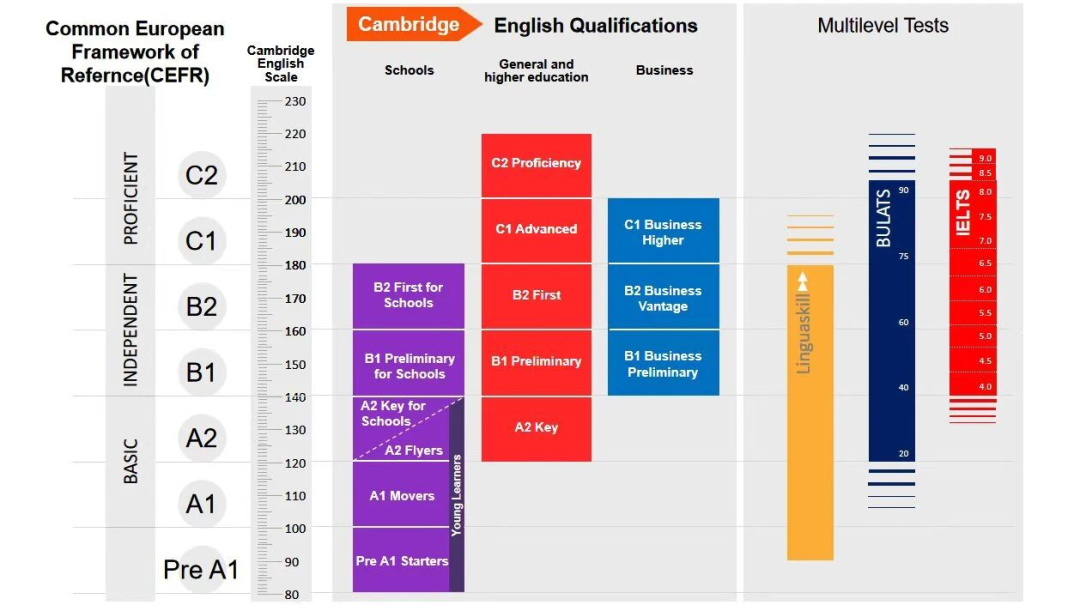近日,特朗普政府向多所高校推送的《高等教育卓越契约》草案引发轩然大波。协议中关于“学生学习”的短短百字条款,将矛头直指高校最基础的教学环节——如何给学生评定成绩。为何一份高校合作协议,会对“打分”这件事如此较真?
协议里的“评分铁规”:理想与现实的撕裂
协议对高校的“评分诚信”提出了双重硬性要求,字面上堪称“学术严谨性的范本”:
- 分数必须成为学业成果的“精准镜像”,严禁因种族、政治立场等非学术因素调整成绩,只能体现学生对学科知识的实际掌握深度与广度;
- 建立全透明的评分问责体系,需公开包含多年趋势的分数分布图表,对成绩异常波动作出说明,并主动与同类院校进行横向对比。
乍看之下,这些要求与教育界倡导的“客观评价”理念不谋而合。《成长导向评分》合著者罗伯特·塔尔伯特直言,前两条表述甚至可能出自教育改革者之手,与政治立场无关。但深入推敲便会发现致命矛盾:协议将分数定义为“客观衡量标准”,而密西西比大学教学卓越中心主任乔希·艾勒指出,现实中分数从来都是基于教学情境的主观判断,这种“客观化假设”本质上是对教育复杂性的简化。
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简化背后暗藏着保守派的价值取向。协议对“纯粹学术评分”的强调,与特朗普政府推崇的“精英治国”逻辑高度契合——默认只要消除“非学术干扰”就能实现公平,却刻意回避了不同学生面临的教育资源差异等根本问题。
分数通胀:被政治化的教育现象
协议的核心矛头指向“分数通胀”这一争议已久的话题,而这一教育现象早已被赋予了浓厚的政治色彩。
- 数据背后的焦虑:美国高校分数上升已成数十年趋势,哈佛大学2024届毕业生中近80%GPA达到3.7及以上,耶鲁大学A及A-成绩占比从2010年的67%升至2022年的 82%。前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萨默斯直言:“哈佛最常见的成绩是A,这在竞争激烈的世界里传递了错误信号”。保守派将此解读为“学术标准衰退”的铁证,认为高校为迎合“政治正确”放松了评分尺度。
- 自相矛盾的解决方案:协议一方面要求分数“基于知识掌握程度”,另一方面又通过公开分数分布遏制通胀,本质上陷入了逻辑分裂。肯塔基大学教授托马斯·格斯基指出,这对应着两种教育定位:前者是“培养者”思维,认为高分可能是教学成功的体现;后者是“筛选者”逻辑,将分数视为区分人才的工具。更关键的是,学界对“通胀”本身仍有争议——北卡罗来纳大学教授伊桑·赫特认为,分数上升可能源于录取标准提高或教学改进,不能简单等同于“注水”。
在保守派叙事中,分数通胀被进一步与DEI(多样性、公平与包容)政策挂钩。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弗雷德里克·赫斯甚至将亲巴勒斯坦学生抗议与分数通胀关联,声称精英院校的“学术放水”与意识形态泛滥互为因果,而遏制通胀成为“重塑学术严谨性”的抓手。
权力博弈:评分背后的学术自由之争
即便认可“规范评分”的目标,高校与学者仍对协议的实施充满警惕,核心担忧集中在政府对学术自主权的侵蚀。费尔利·狄金森大学教授彼得·伯克霍尔德指出两大关键隐患:
- 假想的“评分偏见”:协议宣称要防范教授因政治立场影响评分,但现有研究并未证实这一普遍现象,且高校已建立成熟的分数申诉机制;
- 隐蔽的权力扩张:分数分布本身无害,但“谁来定义正常分数区间”“如何解读波动原因”的权力一旦落入政府手中,风险便随之而来。若数据细化到院系甚至个人,再配套奖惩机制,可能引发“举报教师言论以影响其职业发展”的危机。
这种担忧并非空穴来风。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教授乔迪·格林揭露,协议的评分要求实则呼应了保守派的双重诉求:既指责“精英院校特权学生太轻松”,又暗指“DEI政策让弱势学生获得特殊待遇”,最终指向废除多元化招生的核心目标。而特朗普政府此前已通过行政令强制高校提交招生数据,核查是否“变相考虑种族因素”,此次评分改革可视为其干预高等教育的延续。
争议本质:高等教育的方向之争
这场围绕“学生评分”的博弈,本质是美国高等教育发展方向的分歧。分数看似是教学细节,却串联起学术自由、教育公平与政治干预等多重议题:
- 对保守派而言,规范评分是对抗“政治正确”、回归“精英主义”的突破口,试图通过标准化评价重塑高校“追求卓越”的定位;
- 对高校与自由派学者而言,这是对学术自主权的严重侵犯,担忧政府将评分工具化,最终服务于特定政治议程;
- 对学生而言,评分标准的摇摆直接影响其学业发展——雇主已开始质疑高分背后的真实能力,有数据显示60%的雇主因“能力不符”解雇过Z世代员工。
结语
目前,麻省理工学院、布朗大学、宾大、南加大等名校已明确拒绝签署协议(布朗、宾大、南加大拒绝特朗普政府教育契约,与MIT并肩捍卫学术自由),更多高校仍在权衡。这场看似琐碎的“分数之争”,实则成为观察美国高等教育未来的窗口:是在政府干预下走向标准化的“可量化教育”,还是在学术自治框架下探索更合理的评价体系?答案或许将在政治与教育的持续博弈中逐渐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