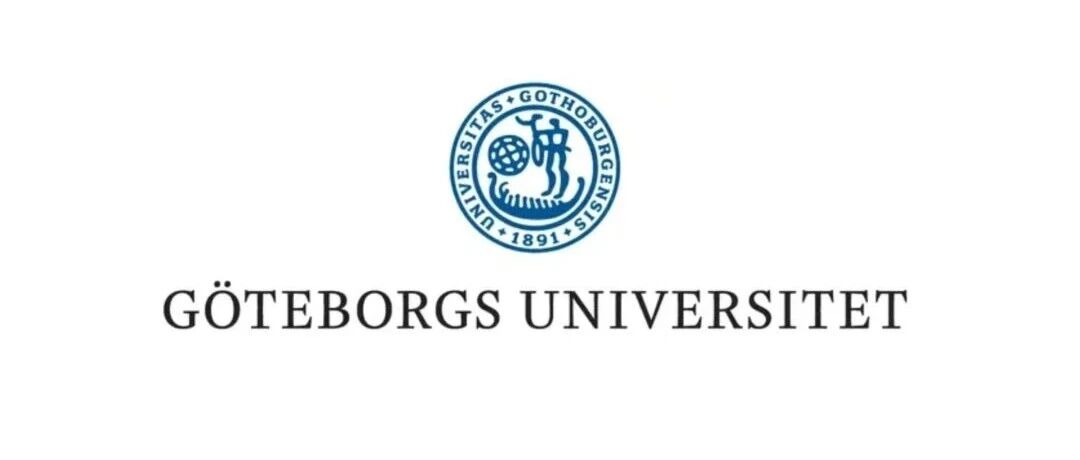招生要求
要加入Barnard教授的课题组,申请者需满足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官网最新公布的博士招生标准,同时契合历史系的专项要求。筛选过程中,“学术背景的匹配度”与“潜在的研究能力”是核心考察因素,具体条件可归纳为以下四点:
- 学术背景:申请者需拥有历史学、东南亚研究、环境研究等相关专业的硕士学位;若为本科毕业,需具备足以证明学术能力的突出成果(如发表过相关领域论文、参与过科研项目)。本科及硕士阶段的GPA需达到NUS规定的最低标准——通常要求二等一荣誉学位及以上,国内高校申请者均分多需在80/85分以上(具体数值以官网当年更新信息为准),完整的成绩单必须提交,以体现学术学习的连贯性。
- 语言能力:对于非英语母语的申请者,托福(iBT)或雅思(Academic)成绩是必备材料。其中,托福总分不得低于90分(单项分数均需超过20分),雅思总分需达到6.5分(各单项不低于6.0分)。若申请者的硕士阶段课程全程以英语授课,可向学校申请豁免语言成绩,但需提供授课语言的官方证明文件。
- 申请材料:四类材料构成申请的核心,缺一不可。第一是个人陈述(Statement of Purpose),其中必须清晰说明个人研究兴趣与Barnard教授研究方向的契合之处;第二是研究计划(Research Proposal),需聚焦具体的研究问题,篇幅建议控制在3000-5000字,以展现研究思路的可行性;第三是2-3封学术推荐信,推荐人须为熟悉申请者学术表现的教授或研究员,推荐信需客观评价申请者的科研潜力;第四是代表性学术成果,如硕士论文、已发表的期刊论文或会议报告,这些材料能直接证明申请者的研究与写作能力。
- 选拔流程:材料通过初审后,申请者需参加由Barnard教授及NUS历史系学术委员会共同组织的面试,面试形式可能为线上或线下。面试环节重点考察三方面内容:研究计划的可行性、对相关领域核心文献的掌握程度,以及申请者与课题组学术方向的适配性。值得注意的是,成功录取者可获得全奖资助,该资助覆盖学费、日常生活费及必要的研究经费,录取后需与Barnard教授共同确定具体的研究方案。
研究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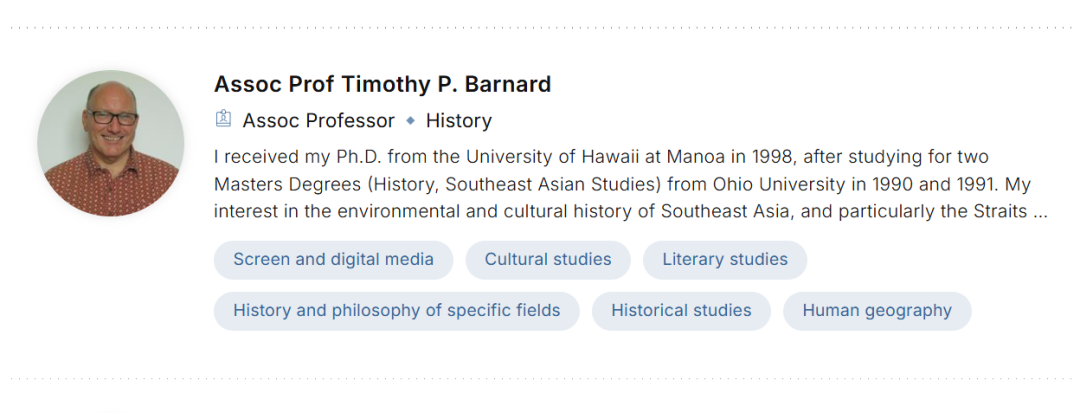
Barnard教授的研究领域聚焦于东南亚历史,且始终以“环境”与“文化”为两大核心支柱,每个研究方向都有丰富的著作与论文作为支撑,学术脉络清晰可见。具体可分为以下三个方向:
- 新加坡环境史(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Singapore):这一方向是Barnard教授研究的核心领域之一,研究时段覆盖殖民时期至当代,重点探索新加坡环境变迁的历史逻辑。他的专著《Nature’s Colony: A History of the Singapore Botanic Gardens》(2016),系统梳理了新加坡植物园的发展历程,揭示其如何从殖民时期的“帝国象征”转变为当代的“生态地标”。在论文《Imperial forests and nature reserves in Singapore, 1883-1959》(2025)中,他进一步分析了1883至1959年间新加坡“帝国森林”与“自然保护区”的设立背景,探讨殖民治理与环境管理的互动关系。另一篇论文《Mosquitoes, Public Health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Modern Society》(2024)则从“蚊子”这一微小生物切入,阐述其与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关联,进而展现新加坡“现代社会”构建的历史过程——这种“以小见大”的研究方法,正是Barnard教授环境史研究的特色所在。
- 近代早期马来世界的社会与环境史(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the Early Modern Malay World):该方向以马六甲海峡及周边区域为研究范围,核心是探索1500年之后马来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动态关系。2024年出版的著作《Singaporean Creatures: Histories of Humans and Other Animals in the Garden City》是这一方向的代表性成果,书中通过梳理“人类与其他动物”的互动历史,揭示了马来世界社会结构与环境变化之间的深层关联。在2022年发表的论文《A Spiteful Campaign: Agriculture, Forests, and Administering the Environment in Imperial Singapore and Malaya》中,Barnard教授还分析了殖民时期的农业政策与森林管理措施如何重塑马来地区的社会-环境体系,为理解当代东南亚的环境问题提供了关键的历史视角。
- 作为历史资料的马来电影(Malay Film as a Historical Source):这一研究方向充分体现了Barnard教授对“非传统史料”的重视,他将1950至1960年代的马来电影视为研究历史的重要材料,而非单纯的文化产品。在他看来,这一时期的马来电影不仅记录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场景,更蕴含着人们对自然环境的认知与态度,还反映了特定的政治语境。通过分析这些电影,可与传统的文字档案形成互补,从而更鲜活地还原历史全貌。目前,他已围绕电影中的“马来身份”建构与“环境叙事”展开研究,为东南亚影视史与社会史的交叉研究开辟了新路径。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Barnard教授的语言能力为其研究提供了显著优势。他的印尼语水平达到“可进行同行评审”的程度,荷兰语与法语则具备阅读能力。由于马来地区在殖民时期曾受荷兰统治,大量官方档案以荷兰语或法语记录,这种语言能力使他能够直接查阅原始档案,从而确保研究的原创性与准确性——这一点,正是他在东南亚历史研究领域保持竞争力的重要原因之一。
Mason博士有想法
基于Barnard教授的核心研究方向,以下三项创新研究计划得以提出。这些计划均遵循“历史议题与当代需求结合”“跨学科方法融合”的原则,既与Barnard教授的学术理念高度契合,又具备明确的研究目标与可行性:
- 计划1:殖民时期新加坡环境治理遗产对当代气候变化适应策略的影响研究
1883至1959年殖民时期,新加坡实施了一系列环境政策,如“帝国森林”管理、自然保护区设立等(这些政策正是Barnard教授此前的研究重点)。那么,这些历史时期的环境治理遗产,对当代新加坡应对海平面上升、城市热岛效应等气候变化问题的策略,是否存在影响?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为解答这一问题,研究将采用“历史脉络分析法”与“案例对比法”。首先,通过NUS图书馆、新加坡国家档案馆获取殖民时期的环境政策档案,包括荷兰语、英语撰写的原始文献,梳理政策的制定背景与实施效果;其次,收集新加坡国家环境局(NEA)发布的当代气候适应政策文件,对比分析两者在治理理念、实施手段上的关联;最后,选取新加坡植物园、南部海岸保护区等典型区域进行实地调研,验证历史遗产在现实中的体现。
这项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它将殖民环境史与气候变化这一当代核心议题相结合,填补了“历史遗产对气候适应策略影响”这一研究空白。其研究成果不仅能为新加坡优化气候适应策略提供历史参考,也能为其他沿海城市应对类似问题提供借鉴。
- 计划2:1950-1960年代马来电影“环境叙事”的数字化分析与历史验证
1950至1960年代,Studio Shaw Brothers、Keris Films等机构出品了大量马来电影。这些电影中呈现的自然环境,如橡胶园、红树林、城市绿地等,是否与同期马来社会的环境变迁(如农业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相符?电影中的“环境叙事”能否作为研究当时社会环境的有效史料?
研究将分两步展开:第一步是“数字化分析”,与新加坡国家档案馆合作,对该时期30-50部马来电影进行数字化处理,再运用影像内容识别等数字人文工具,提取电影中的环境元素,统计不同环境场景的出现频率与呈现方式;第二步是“历史验证”,收集同期马来亚殖民政府发布的农业报告、报纸报道等文字史料,对比分析电影中的环境叙事与现实环境变迁的一致性。
该计划的创新价值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它首次将数字人文技术应用于马来电影史研究,拓展了影像史料的分析维度;另一方面,通过文字史料与影像内容的相互验证,能更准确地还原战后马来社会的环境变迁,为东南亚社会史研究提供更丰富的证据。
- 计划3:新加坡长尾猕猴(Long-tailed Macaques)的“城市动物史”(1819-2024):一项跨学科研究
自1819年新加坡开埠以来,长尾猕猴的栖息地发生了显著变化,从最初的森林逐渐转向城市公园、居民区周边。这种栖息地的变化,是否能反映新加坡“花园城市”建设过程中“人类-动物关系”的演变?不同历史阶段,人类对长尾猕猴的态度与管理方式又有何不同?
研究将延续Barnard教授在《Singaporean Creatures》中提出的“人类与其他动物互动史”框架,融合历史学、生态学与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历史学层面,通过殖民时期的动物管理档案、政府公告,梳理早期人类对猕猴的认知与管理措施;生态学层面,收集新加坡野生动物保护局发布的猕猴种群数量变化数据,分析栖息地变化对猕猴生存的影响;社会学层面,设计问卷调查,了解当代公众对猕猴的态度与互动方式。
这项研究的创新点在于,它以长尾猕猴这一单一物种为研究对象,实现了“微观史”与“宏观城市史”的有机结合。通过梳理猕猴与人类的互动模式,不仅能为“城市生物多样性”研究提供历史视角,也能进一步丰富Barnard教授开创的“城市动物史”研究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