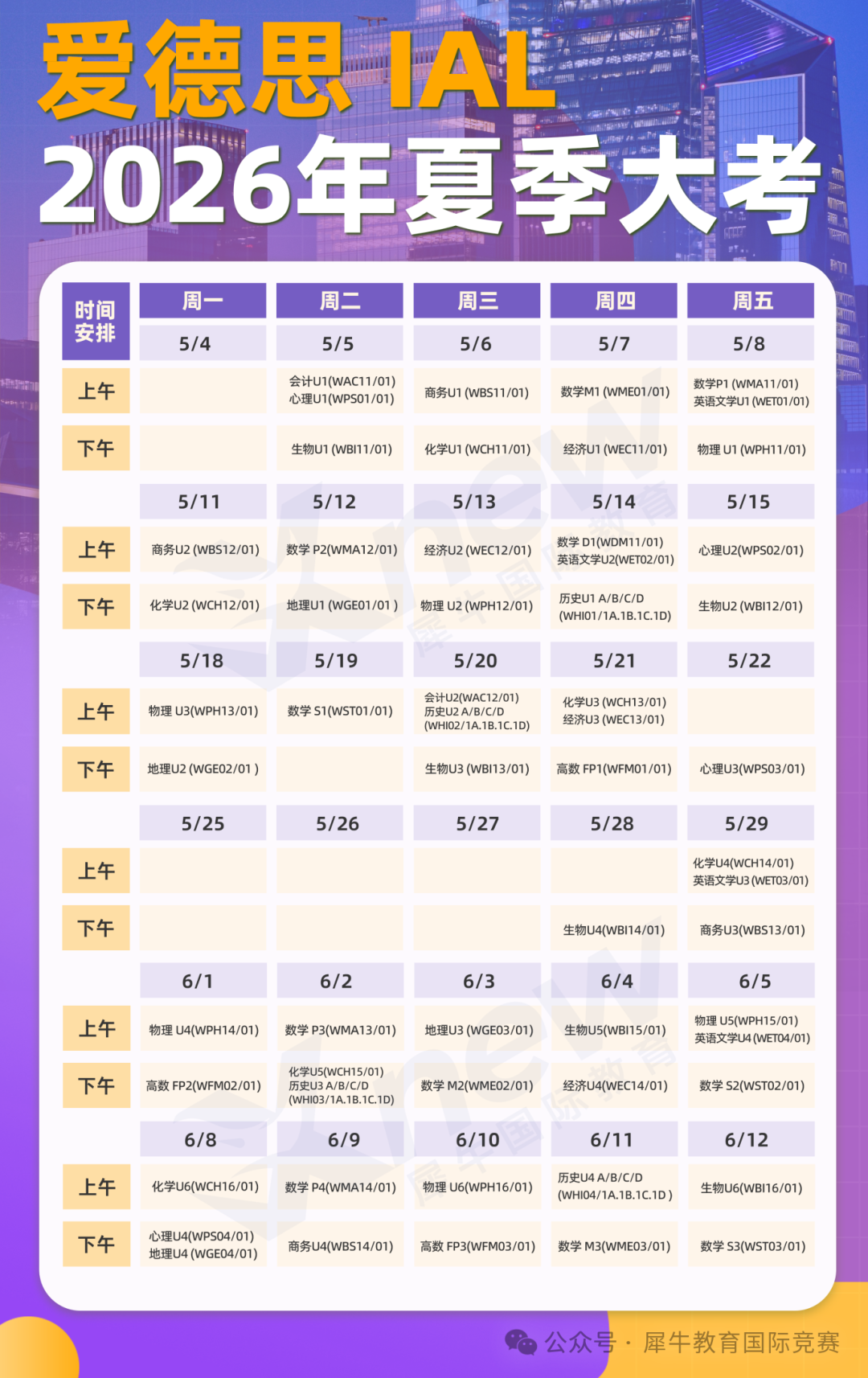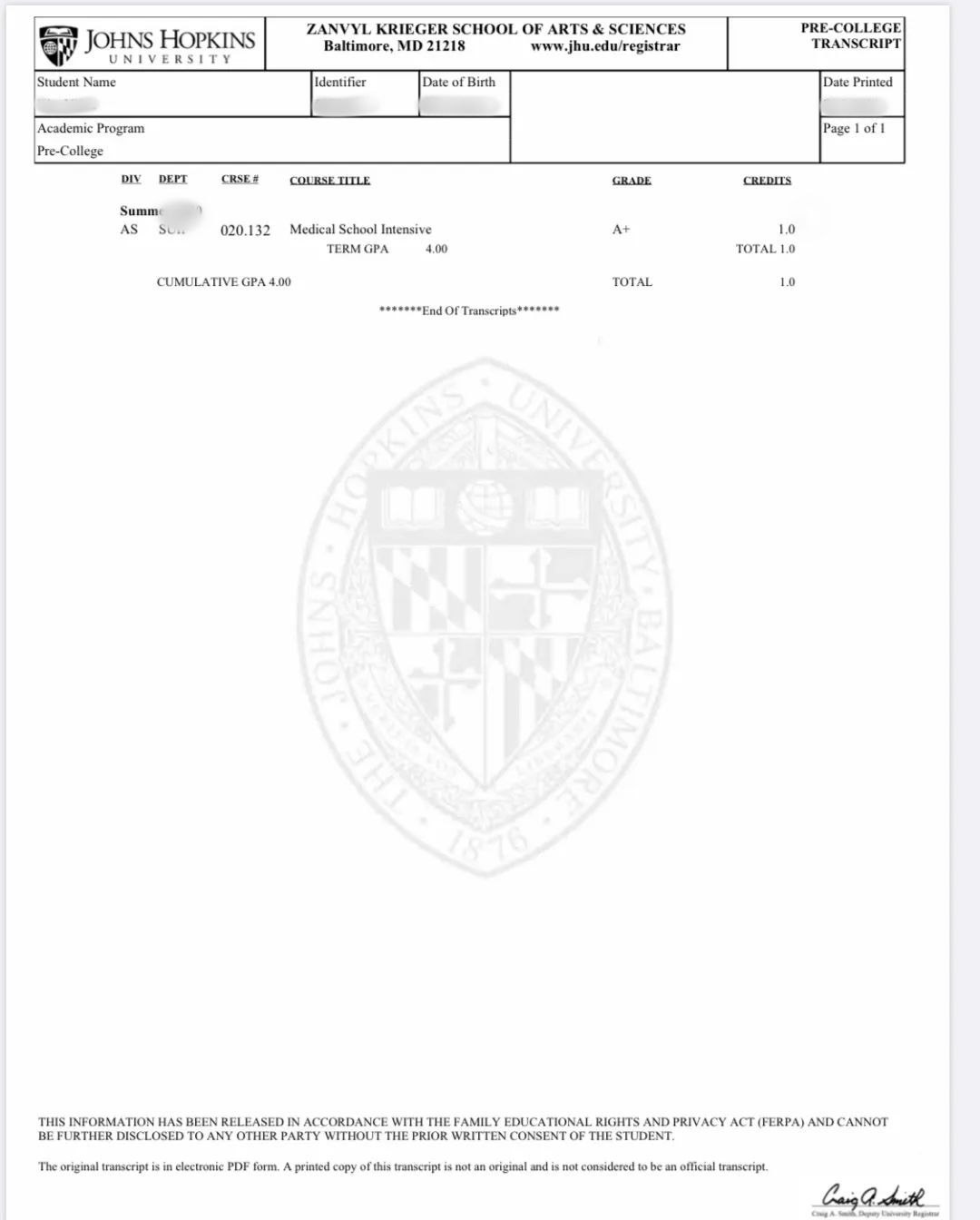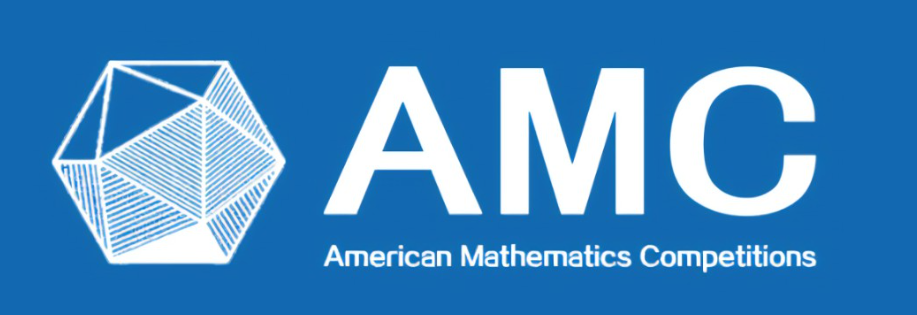凌晨两点,实验室的灯依然亮着。电脑屏幕前,研二的一名学生揉了揉酸胀的眼睛,第N次修改导师临时要求的论文图表。他的打卡记录显示,过去一个月,他的日均工作时长超过12小时,没有周末,没有加班费,甚至没有一句明确的“辛苦了”。
“导师说这是学术训练的必经之路。”他遭遇并非孤例。在近期乌鲁木齐召开的“工商业与人权的理论和实践”学术研讨会上,西南政法大学张教授一针见血:“当剥削被包装成‘培养’,实质是权力不对等下的资源掠夺。”
在高校和科研机构,研究生、博士生甚至部分青年教师,长期处于一种隐形的剥削体系中:超时工作、无偿劳动、成果被占有、精神高压……然而,这些现象往往被“学术理想”“科研训练”等话语合理化,成为默认的“行业规则”。
今天,我们就来拆解这套“合理化"话术,看看实验室里的免费劳动力是如何被系统性地包装成“理所当然”的。
01、“自愿”的陷阱:当剥削披上理想的外衣
(1)“做科研就要吃苦”的神话
在学术圈,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叙事:“真正的科研人必须全身心投入,996是福报,007是常态。”导师们常以“我当年也是这么过来的”来合理化高强度工作,而学生则被灌输“不吃苦怎么出成果”的思维。
但问题在于:“吃苦”不等于“被剥削”。真正的科研训练应包括思维培养、方法学习,而非单纯的体力劳动(如报账、取快递、帮导师带孩子)。2021年,《Nature》针对全球3,200名博士生的调查显示,76%的人每周工作超过50小时,但近半数认为自己的劳动未被合理回报。
2025年6月发布的《导师压榨经济学》研究报告揭示:65%的硕士生周工作时长超法定标准,其中生物化学领域高达82%。更触目惊心的是,83%参与完成的专利以导师为第一申请人。
这种剥削通过三重异化完成:
①时间异化:某985高校实施“打卡坐班制”,文科生被要求每天实验室“坐满”10小时;
②智力异化:博士生的课题被迫转向导师承接的横向项目,学术兴趣让位于商业需求;
③成果异化:论文署名遵循“导师永远通讯+师兄师姐优先”的潜规则。
(2)“为你好”的话术
“多干活是锻炼你”,“现在辛苦点,以后简历好看”——这些话术将剥削包装成“投资”。
但现实是:许多“额外工作”与学生的研究方向无关。某985高校博士生匿名爆料,导师让他连续半年整理无关项目的发票,理由是“培养细心”。
(3)“情怀税” ——用理想主义掩盖劳动力再生产
导师最爱在组会说:“我们搞科研不是为了钱。”但转头就会在群里发:“学校财务说劳务费超过800要交税,大家体谅一下。”——原来情怀税的税率是20%,而且只收学生。
更魔幻的是,当你质疑“为什么我的补贴比食堂阿姨还少”时,会有人语重心长:“你总不能和阿姨比吧?她可是有编制的。”那一刻,你终于懂了:在学术金字塔里,编制是比IF值更硬的通货。
02系统的合谋:谁在维持这套规则?
(1)导师的“权力垄断”
在实验室“小王国”里,导师掌握着绝对权力:毕业签字、推荐信、科研资源分配。学生不敢反抗,因为反抗成本太高——轻则被冷落,重则延毕。2022年,华中某高校一名硕士生因拒绝帮导师做横向项目被威胁“别想毕业”,最终选择退学。
(2)学校的态度
高校的考核体系加剧了问题。学校看重论文数量和项目经费,导师为了达标,自然将压力转嫁给学生。而学生投诉机制形同虚设:多数高校的“师德委员会”由教授组成,难以中立。
更讽刺的是,研究生补助常年低于最低工资。2023年,某Top 10高校的博士生每月津贴仅3,000元,而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为2,480元。校方的解释是:“科研津贴不是工资,是培养支持。”
(3)师兄的“时间复利”陷阱
实验室的层级像俄罗斯套娃:博后压榨博士,博士压榨硕士,硕士压榨本科生,本科生……只能压榨那只永远洗不干净的研钵。
最惨的是“传承式剥削”——师兄A当年被师兄B压榨,如今他成了B的“学术代理人”。“我当年可是徒手包过500个胶的!”A拍着肩膀对你说,语气像在传授葵花宝典,而不是告诉你:他当年包的500个胶,有300个现在还在-20℃冰箱里当文物。
(4)同辈的“内卷”合理化
“别人能熬,你为什么不能?”——这种氛围让学生自我PUA。某匿名论坛上,一名博士生写道:“看到同门通宵做实验,我也不敢早走,怕被说不努力。”当剥削成为常态,拒绝剥削反而成了罪过。
03反抗的可能:如何打破沉默?
(1)识别“有毒”实验室的预警信号
①导师常把“学术理想”挂在嘴边,却从不提劳动报酬;
②实验室文化强调“感恩”,反对谈权利;
③高年级学生默认“熬出头就好”,但无人真的熬出头。
(2)用法律和制度武器
①《劳动合同法》:如果参与导师公司的项目,可主张劳动关系(已有胜诉案例);
②高校投诉渠道:教育部明确禁止导师让学生承担无关劳务(2020年《研究生导师指导行为准则》);
③学术共同体曝光:Nature、Science等期刊近年增设“学术不端”举报机制。
(3)建立互助网络
像国内开始出现匿名文档记录导师压榨行为。集体发声比个体抗争更有效。
(4)发明“学术分摊”概念
当导师说“这个实验很简单”时,立刻追问:“请问这个‘简单’的实验,占我毕业课题工时的公摊面积是多少?是否需要我签署《学术物业协议》?”用魔法打败魔法,用官僚主义对抗官僚主义。
结语:贵州新条例中“尽职免责”条款的深意值得思考——它明确科研人员“履行勤勉尽责义务仍不能完成高风险项目的,予以免责”。这条款像一把钥匙,解开的不仅是创新枷锁,更是对学术成功学的祛魅。
当我们看到浙江“科技副总”带着研究生深入企业车间,当白马湖实验室的股权证书出现在年轻研究员的抽屉里,当区块链存证使一篇论文的贡献度如水晶般透明——学术剥削的堡垒正在新一代科研人的觉醒中松动。
乌鲁木齐研讨会上,那句被掌声淹没的宣言或许预示未来:“实验室不是封建领地,知识生产拒绝血汗工厂!”学术不该是血汗工厂。科研需要热情,但热情不该被滥用。当我们把“免费劳动力”视为常态时,伤害的不仅是学生,更是整个学术生态——当年轻人因压榨逃离科研,最终埋单的是整个社会的创新能力。
下次听到“做科研就要吃苦”时,不妨反问一句:“为什么我们不能既要热爱,也要公平? ”
你在实验室遇到过隐形剥削吗?欢迎在评论区匿名分享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