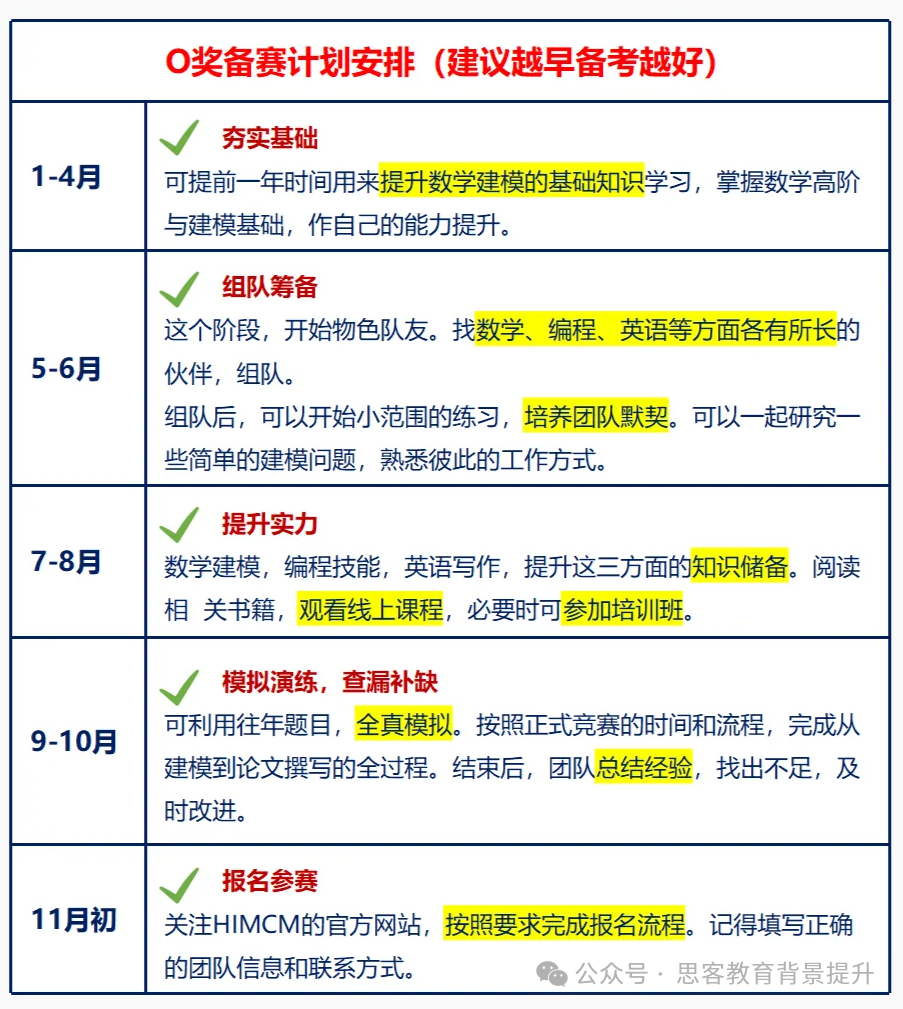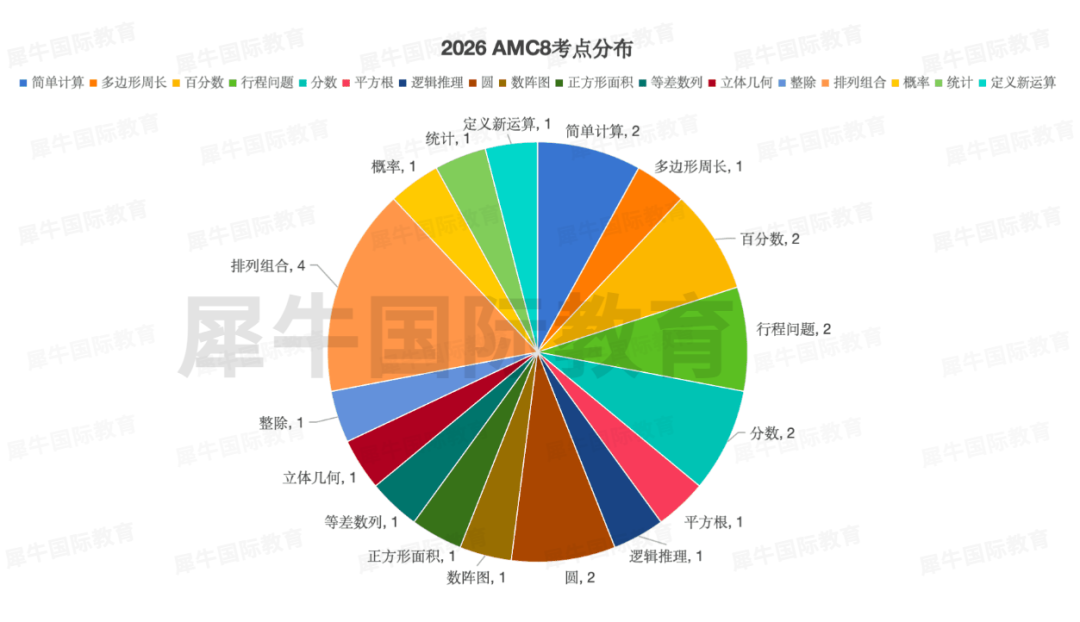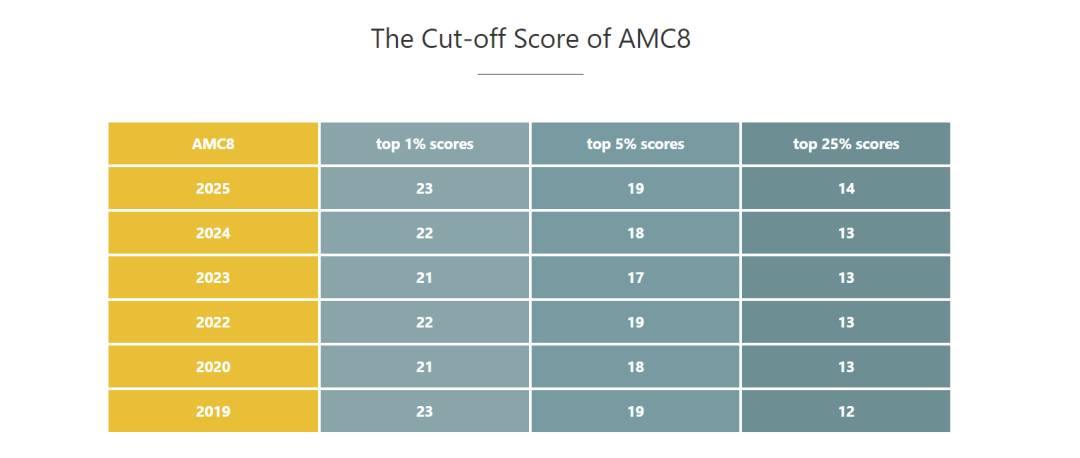【编辑推荐】当人工智能对传统人文课堂形成冲击,担忧之声四起之时,《纽约时报》观点撰稿人杰西卡·格罗斯发现,一些教授们正在选择积极行动。他们不再执着于禁止AI工具,而是重新设计课程,将口试、社区实践、课堂项目与透明规则相结合。这些创新教学不仅帮助学生重建疫情后亟需的社交与认知能力,更致力于在技术洪流中守护人文教育的核心价值——思想碰撞、深度联结与人的真实力量。我们一同来看看这些先行者的探索。
今年以来,我一直在阅读一些文章,它们描绘了人工智能时代人文学科教学的“末日”景象。文章大多讲的是同一个故事:没有人能阻止大学生利用像ChatGPT和Claude这样的聊天机器人来总结阅读材料、写作论文,任何试图阻止的努力都是徒劳的。对于非专业的人文学科学生来说,这门学科基本上已经没救了。
人工智能冲击人文教学
有些教授也开始借助这项技术走捷径。正如《纽约杂志》的詹姆斯·D·沃尔什在一篇广受关注的文章《每个人都在大学里作弊》中指出的,这种情况“令人不禁怀疑:现在是不是人工智能在评估人工智能写的论文,整个学术活动看起来就像是两台机器人在对话——甚至可能只是单方面的‘机器人自言自语’。”
诚然,大型语言模型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改进,这项技术也将长期存在。但在我此前的专栏里提到教授们如何应对人工智能后,来自全国各类院校的约100位大学教授给我发来了电子邮件。过去一周,我与几位教授深入聊了聊 ,他们教授英语、哲学、伦理学、音乐、宗教、艺术,甚至游戏设计等课程,并且正在将他们的课程重新构想成更具人文关怀和实用价值的东西。
这些教授坦言,人工智能并非他们改变教学方式的唯一动力。他们的学生——尤其是2020-21学年就读高中的学生,他们的社交和认知能力已经萎缩,而帮助学生重建这些能力成了教授们的使命。
疫情前,我采访的这些教授大多沿用着我20年前上大学时的教学方法:讲课、大量阅读材料和课后论文。但在学生们被迫回家学习,以及近几年ChatGPT变得无处不在之后,他们意识到老办法行不通了。
他们必须想办法确保学生真的在学知识,并且这些知识对他们有意义。简单地禁止人工智能是不行的;他们必须通过让许多作业在课堂上实时完成,无需电脑介入,从而抵御人工智能的影响,同时还得针对其他场景制定一套切实可行的技术使用规则。回想我自己21世纪初读英语专业时写的那些论文,我并不觉得创造它们给我带来过什么特别的启发,但听到这些教授们讲述如何适应人工智能驱动的世界,我不禁怀疑这种论文独创性是否已经过时了。
创新教学与社区实践
通过口试、一对一讨论、社区参与和课堂项目等多种方式,这些教授正在为21世纪的学生们提升人文学科的学习体验。
“我的许多同事都灰心丧气、满腹牢骚。但我不能那样。”犹他谷大学哲学教授克里斯·魏格尔说道。犹他谷大学是奥勒姆一所大型公立院校,同时开设社区学院课程和四年制学位项目,近40%的学生是家里第一代大学生。
魏格尔教授伦理学课程,其中包括一门人工智能伦理课。她向我讲述了她与当地一家青少年危机短期收容所负责人的合作。在犹他谷大学举办的一次社区集市上,该负责人听说了魏格尔教授的授课内容,觉得由他指导的青少年们会对探讨重大问题充满热情。于是,魏格尔教授的通识伦理学课程学生的期末作业是将他们学到的概念传授给这家收容所的青少年,并组织他们进行伦理辩论。
“我强忍住喜悦的泪水,因为我的学生们和那些孩子互动的画面太美好、太鼓舞人了,”魏格尔告诉我,“而且收容所的孩子们也特别投入,他们感受到自己如此受重视、被认可。”她感觉学生们为这次期末考试所做的准备,远远超过了为传统考试或论文所做的努力,因为他们不想让这些青少年失望。
在威斯康星州的小型私立文理学院贝洛伊特学院,英语系教授塔玛拉·凯塔布吉安通过一个名为“社区连接”的项目,在她的学生中也取得了类似的成功。凯塔布吉安描述了她设计的一门“关于科幻小说、世界观构建和厄休拉·勒古恩”的课程,特别是她的小说《一无所有》,这本书“讲述两个互不往来的星球的故事,非常适合秋季举行的2024年大选”。作为课程的一部分,学生们要去图书馆、公立学校和老年中心组织关于这部小说的讨论会。
“课程的关键环节是学生们在外展活动前进行练习和角色扮演,”凯塔布吉安告诉我,“之后,他们还要反思从这些经历中学到了什么、哪些地方可以改进,以及如何向潜在雇主描述自己新掌握的技能。”
AI时代的信任与规则重建
学生们仍然有一些传统的阅读和写作作业,凯塔布吉安并没有完全禁止他们在这些作业中使用人工智能。相反,由于整个学校没有固定的规定,她让学生们围绕人工智能的使用制定了自己的行为准则。“经过相互商讨,他们达成共识:可以用人工智能查阅课程相关的现有学术资料,但不能用它生成书面作业中的具体内容。”
这也是我采访的教授们一个共同点:他们意识到,在人工智能时代,唯一的前行之道就是在课堂上建立对这项技术使用的信任和透明度,而这往往需要结合学生的意见来制定规则。在大学里,监管表面上已经成年的学生使用人工智能,对任何教师来说都不是时间的最佳利用方式。而且,由于人工智能检测软件存在缺陷,教师还有可能冤枉没作弊的学生。
教授们还谈到,学生迫切需要围绕大型语言模型开展媒体素养教育——包括了解其局限性和幻觉问题。这是学生们在上大学前就应该学习的东西。此外,让学生学会批判性地看待这些模型的训练数据也很重要。
图片来源|EuroSchool
不过,告别传统的大学论文和创意写作并非没有弊端。大卫・恩斯明格教授在得克萨斯州贝敦市两年制院校李学院教英语、人文学科和民俗学。他尝试过允许学生完全使用人工智能,却发现他们往往更偏爱传统的、非数字化的方式。因为他和学生都担心人工智能会削弱人类的各项技能,包括阅读长篇文本以及运用正确的语法、拼写和句子结构进行写作。
人文教育的复兴
那么,大学生们该何去何从?Z世代并没有放弃人文艺术,也没有放弃阅读和独立思考的乐趣。随着人工智能在入门级就业市场上制造混乱和不确定性,更多的学生可能会选择追随自己对人文学科的热情;如果学技术或商科甚至都不能保证就业,那何必勉强自己去学习这些专业呢?有迹象表明,人文学科院系在经历长期衰退后正在复苏。被誉为全美顶尖公立大学之一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其艺术与人文学科部的主修人数在过去四年中增长了近50%。
凯塔布吉安给我讲了一个故事,充分展现了在人文教育中人性的力量。她讲述了一个学生的故事,因为害怕当众演讲,这位学生对要在图书馆主持勒奎恩小说的讨论感到极度焦虑。凯塔布吉安指导她克服了恐惧,结果她在主持讨论时表现得非常出色,甚至加入了图书馆的读书小组去结交新朋友。
这正是人文学科应有的样子:融入社区、探讨思想、建立知识纽带。我们不需要把这些拱手让给人工智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