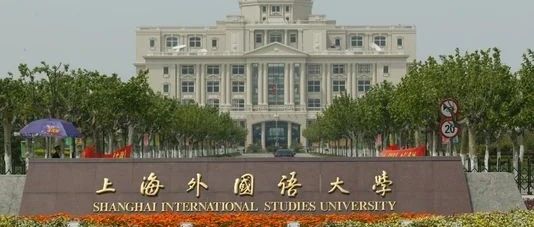八年前的今天,2017 年 5 月 14 日的上午,巴黎的天空还带着初夏的凉意。年轻的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和夫人布丽吉特并肩走进爱丽舍宫,那是一幅经典的交接画面。此刻的法国社会弥漫着期待:这位39岁的新总统,会给这个国家带来怎样的改变?
几个月后,在索邦大学的大礼堂里,马克龙发表了一篇被反复引用的演讲。在那场长达一个多小时的欧洲政策演说中,他说出了那句著名的话:
« Nous devons créer des universités européennes, un réseau où les étudiants pourront circuler librement, apprendre et bâtir l’avenir de l’Europe. »“我们必须创建欧洲大学,一个网络,让学生们可以自由流动、学习,并共同建设欧洲的未来。”
在那一刻,法国大学的改革似乎被赋予了一种新的使命感:不只是为了国内的竞争,而是要在世界高等教育的舞台上,扮演一流的角色。
事实上,一切并非始于 2017,法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号角,在马克龙之前早已吹响。
- 2007 年,萨科齐政府推动LRU 法案,大学校长首次掌握了实权,预算和人事不再完全受制于教育部。这是法国大学“自主化”的开端。
- 2010–2011 年,法国推出卓越计划(IdEx),政府豪掷数十亿欧元,要在国际舞台上打造几所“世界级大学”。波尔多、斯特拉斯堡、巴黎科学与文学联盟(PSL)等率先入选。
- 2013 年,奥朗德政府的Fioraso 法案强制各地高校组成COMUE,合并浪潮随之展开。艾克斯-马赛、波尔多、格勒诺布尔,接连出现“大校”。
这些年,法国大学经历了合并、重组、联盟,甚至学生抗议,但目标始终清晰:让法国的大学,不再在世界排名和科研声望上“掉队”。
再回头看这八年,真的是百年巨变的年代。英国完成脱欧,欧洲格局震荡;新冠疫情让全球教育体系按下暂停键;俄乌战争持续重塑地缘政治;经济危机与通货膨胀则考验着各国财政。法国的大学改革,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推进的。能保持连续性,本身就并不容易。
在这不平静的八年,法国的教改又迈出怎样的步伐呢?
2017 年,IdEx 第一轮评估完成,几所项目被终止,但巴黎、波尔多、斯特拉斯堡挺过了考验。与此同时,政府确立了EPE(实验性公共机构)的法律框架。
2019–2020 年,成效显现:
- Paris Sciences et Lettres(PSL)首次进入 QS 世界前 50。
- Université Paris-Saclay在《上海排名》中一举跻身全球前 15,在数学、物理等学科甚至进入前五。
- Université Grenoble Alpes也借合并和 IdEx 支持,进入国际百强。
2021 年之后,欧洲大学联盟(European Universities Initiative)逐渐成型,法国有 40 多所高校参与,数量居欧洲前列。这意味着法国大学改革不只是国家战略,而是被纳入欧盟的大棋局。
2024–2025 年,又一轮结构性调整发生:
- Université de Franche-Comté改名为Université Marie-et-Louis-Pasteur,以“巴斯德”之名打造新品牌。
- Université de Toulouse升级为 EPE,成为覆盖西南大片地区的超级大学。
- 蒙彼利埃三大、尼姆大学、圣艾蒂安大学、布列塔尼大学等,也相继转为 EPE。
- 与此同时,COMUE 模式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八年下来,法国大学的地图,已经与 2017 年时截然不同。如果说 2017 年的法国大学,还在为“如何在国际舞台上被看到”而焦虑,那么 2025 年的它们,至少已经拥有了几张能拿得出手的名片。
在排名上,2017 年时,法国高校普遍徘徊在百名之外。巴黎综合理工(École Polytechnique)是少数还能进入前 60 的学校,而巴黎六大(UPMC,后来并入索邦大学)也只是勉强在世界前 150。八年过去,局面明显改观:PSL 已经稳定在 QS 前 30,巴黎萨克雷也跻身世界前 70,索邦大学、格勒诺布尔、斯特拉斯堡则稳居百强到一百五十之间。法国终于有了在榜单上“亮眼”的几所大学。相比八年前,整体向上了一档。
在留学生规模与吸引力上,2017 年法国接收的国际学生大约是 32 万人,如今已突破 43 万,增幅接近三分之一,位居世界第六,仅次于美英澳加德。中国学生依旧是最大群体,但近年来非洲和欧洲邻国的比例显著上升。奖学金政策、英语授课项目与低学费,仍是法国吸引力的重要支撑。
在科研成果上,八年前法国依旧依赖传统强项——数学、物理和基础科学,虽然底子厚,却缺乏新的国际突破。到 2025 年,巴黎萨克雷的数学位列全球第一,物理学科进入前五,格勒诺布尔的材料科学与信息学也跻身欧洲前列。法国学者继续活跃在诺贝尔奖、菲尔兹奖的榜单上,科研“尖峰”依旧坚挺。法国当然难以与中美的科研体量相比,但在欧盟科研框架的放大效应下,它稳固了几个关键领域的全球话语权。
然而,说到八年的成绩,也不能回避它的局限。法国大学再怎么努力,也始终摆脱不了一些“结构性的掣肘”。
首先是体量问题。法国的人口和财政总量注定无法与中美相比,更直接的差距在于科研投资的规模与集中度。美国的顶尖大学动辄掌握数十亿美元的校友基金,中国的“双一流”计划可以一声令下,把资源火力集中投向少数几所学校。而法国的高教体系,长期坚持低学费与均衡支持,财政的蛋糕有限,还要尽量切得平均。结果是,它很难在全球造就几所“超级巨头大学”,更多的是维持一个稳固的中坚梯队。
其次是制度问题。法国的教育治理天生是“分权与多元”的:大学有法定的自主权,科研院所(CNRS、Inserm 等)自成体系,Grandes Écoles 和综合大学平行存在。资源分散,竞争与协作并存,国家难以像中国那样“一锤定音”,把顶尖师资和资金一股脑投向一两所旗舰学校。这种模式的好处是整体均衡,坏处则是缺少那种“集中突破”的爆发力。
最后是文化差异。法国高教深受人文与共和传统影响,它强调知识的公共性,抗拒过度市场化;法语世界坚持“文化例外”,既参与全球体系,又对英语的主导保持警惕。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大学是企业化的竞争者;在法国,大学依旧是共和国的公共机构。这让法国高校在国际排名和品牌营销上常常显得格格不入,但也保留了另一种教育价值观。
所以说,小马这八年,单从高等教育改革来看,确实做了不少事:大学合并有了规模,排名有所提升,国际学生数量稳步增长,科研也在某些领域保持了声望。只是如果把视野放到更大的世界范围里,这些动作看上去又显得微小,似乎法国依旧停留在“原地踏步”。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它无所作为。恰恰相反,法国在高教领域持续的努力,让它在欧洲乃至全球教育格局中扮演着一种独特的角色。它没有办法像美国那样靠体量碾压,也不像中国那样集中力量攻坚,但它凭借欧盟平台放大了自身影响力,用一种缓慢而稳定的方式,守住了教育的公共性与多样性。
古人说“有教无类”,孔子两千多年前就把教育的普惠性写入理想。而在西方,孔多塞在《全民教育五个纲要》中也断言:“让所有人都能拥有满足自身需要、保障幸福、了解并行使权利的手段。”中西先贤跨越时空传递出的共识,正是教育最朴素也最恒久的信念。法国大学的坚持,让人看到这份理想仍有人践行,仍能办好学,教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