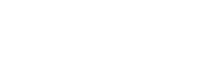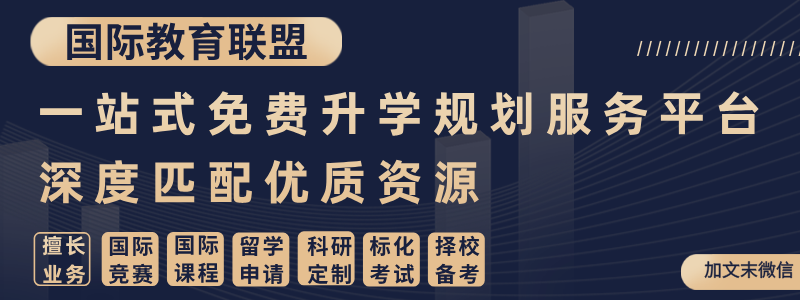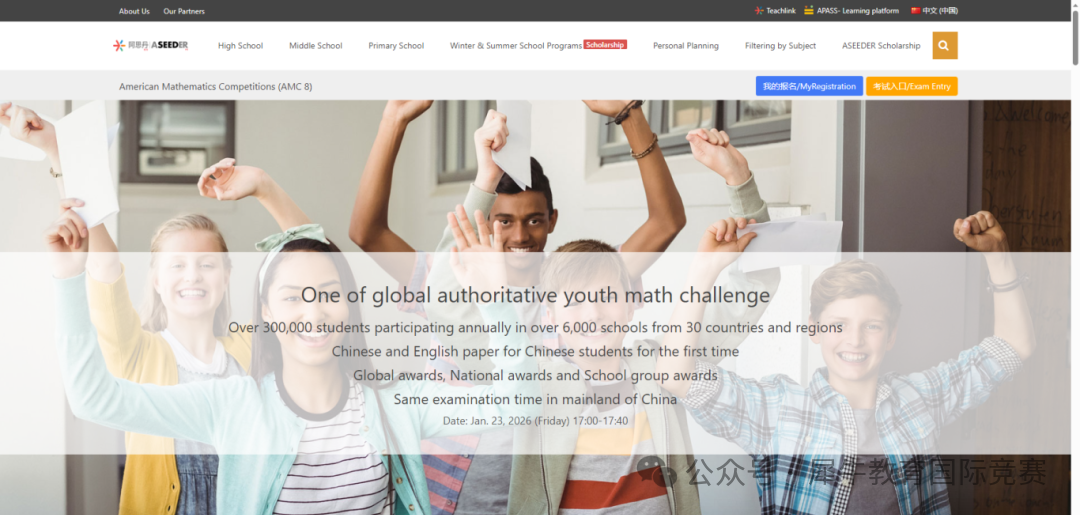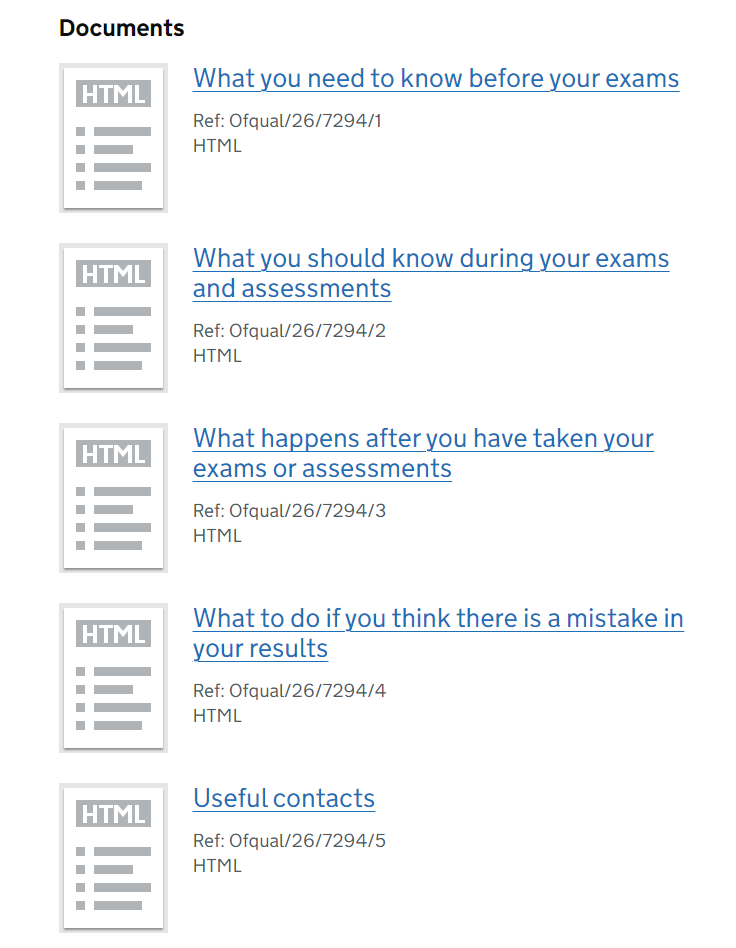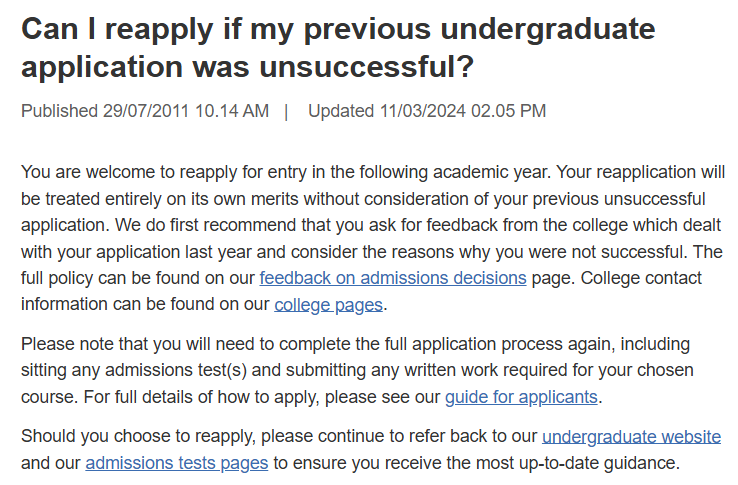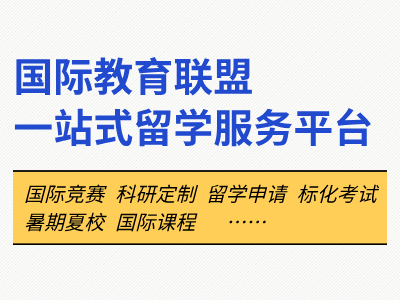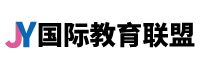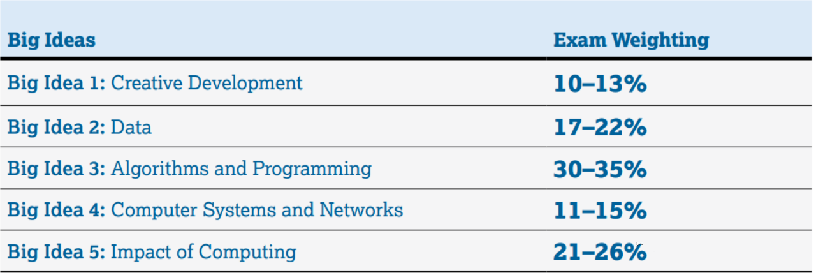在关于“内卷”的全球大讨论中,瑞典貌似选择“退出群聊”。
我们熟悉的叙事是:成功源于超常的苦难与付出。凌晨四点的城市、睡在公司行军床上的创业者、牺牲假期换来的指数级增长……这几乎是东亚经济腾飞的标配。
但在瑞典,这一切似乎都失效了。
这里的人均年工作时长仅为1400多小时(相比之下,OECD数据显示日韩国往往超过1600个小时,中国甚至很多行业往往超过2000小时); 这里有令人咋舌的假期制度,7月几乎全民“失联”去度假; 这里的职场极其强调“Work-Life Balance”,下午接孩子比开会更重要。
按常理推断,这样一个“养尊处优”的国家,经济活力应该很差。但实际上呈现的结果却出乎意料。
瑞典是全球人均产出“独角兽”企业(估值超10亿美元的初创公司)第二高的地区,仅次于硅谷。 Spotify(音乐流媒体)、Skype(网络通讯)、King(《糖果传奇》开发商)、Mojang(《我的世界》开发商)、Klarna(金融科技)、Scania(卡车巨头)……这些改变全球生活方式的公司,全都来自这个人口仅1060万(约等于中国杭州市)的北欧小国。
Credits: Margareta Bloom Sandebäck/Imagebank.sweden.se
为什么一个看起来“最懒”的国家,却成了全球最顶尖的创新高地之一?
在撕开“北欧童话”的滤镜后,我们发现瑞典的成功并非仅仅源于“松弛感”,而是一套精密、昂贵且并非完美的社会系统运转的结果。它在带来极高创新率的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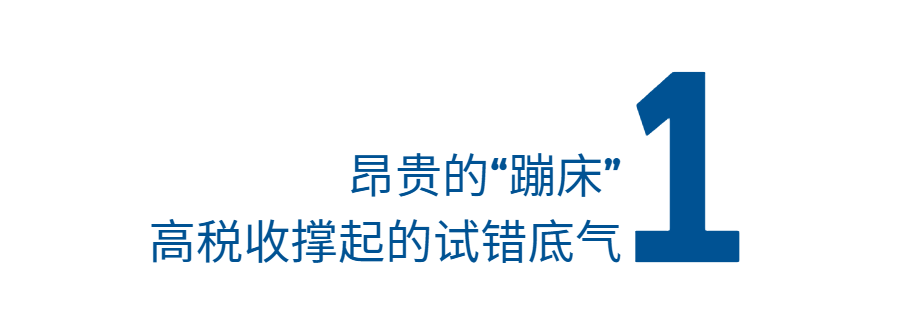
提到瑞典,很多人第一反应是“高福利养懒人”。的确,瑞典有着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体系,但这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它的代价是极高的税收负担。瑞典的个人所得税边际税率最高可达50%以上,这意味着你赚的每一块额外收入,可能有一半要上交给国家。
对于追求巨额财富积累的人来说,瑞典并不友好。宜家创始人英格瓦·坎普拉德曾因不堪忍受高额税收而“出走”瑞典数十年。
但硬币的另一面是,这种高税收撑起了一张极其坚实的社会“安全网”。对于创新创业者而言,这张网不是让人躺平的“吊床”,而是鼓励你向上跳跃的“蹦床”。

Credits: Simon Paulin/imagebank.sweden.se
在许多国家,创业是一场豪赌。失败可能意味着倾家荡产、连累家人、失去医疗保障。这种巨大的“后顾之忧”,让绝大多数有想法的年轻人最终选择了稳妥的打工之路。
而在瑞典,创业失败的“物理成本”被压到了最低。
即使公司破产,你依然享有几乎免费的医疗,孩子依然可以免费上学(包括大学),失业救济金能保障你的基本生活体面。瑞典语里有一个词叫“Trygghet”(安全感/免于恐惧的自由)。当生存焦虑被从大脑中移除后,人们才敢于去尝试那些“看起来很蠢”但可能改变世界的想法。
Spotify的创始人Daniel Ek在创办公司前经历过多次创业尝试。如果他生活在一个“手停口停”的环境中,很难想象他能有足够的耐心和底气去和顽固的全球唱片工业死磕数年。
瑞典模式的逻辑是:通过高税收收束了暴富的可能性,但同时也降低了居民对破产的恐惧感。(不至于最后达到某国存在“斩杀线”无奈局面。)这恰恰是早期创新最需要的土壤。

瑞典职场最著名的文化标志是“Fika”(咖啡小憩)。
每天上午十点、下午三点,雷打不动,大家放下手头工作,聚集到茶水间喝咖啡、吃肉桂卷、闲聊。
Credits: Anna Hållams/imagebank.sweden.se
在追求极致效率的管理者眼中,这简直是严重的资源浪费。明明可以发邮件说清楚的事,为什么非要在那闲扯?
但瑞典人坚持认为,Fika不仅仅是休息,更是一种非正式的信息交换机制。
在等级森严的公司,信息流动往往需要层层审批。但在Fika时间,CEO可能就站在实习生旁边排队接咖啡。一个困扰研发部几周的技术难题,可能在和市场部同事闲聊吐槽时,被对方一句无心的话点醒。信息磨损在 Fika 中降到最低,也突破了各层级的交流壁垒。
创新往往发生在跨学科、跨部门的非正式碰撞中,而不是在紧绷的PPT汇报会议上。
然而,我们也要客观看到这种文化的“副作用”。
瑞典职场极其强调“共识文化”(Consensus Culture)。
为了照顾每个人的感受,瑞典公司往往会陷入无休止的会议中。一个简单的决策,可能需要反复讨论,确保每个人都没有强烈反对意见才能通过。这导致瑞典企业的决策速度在很多时候慢得令人抓狂。
但在需要长周期投入的研发创新领域,“慢”不一定是坏事。它避免了拍脑袋式的盲目决策,一旦达成共识,执行起来阻力极小。
瑞典是用“决策效率”的牺牲,换取了“创新质量”的提升。

瑞典文化的核心基石之一是“詹代法则”(Jantelagen)。它的核心思想非常反精英主义:“不要以为你比别人更特别/更聪明/更优秀”。
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极其压抑的文化。在瑞典,过度炫耀财富、才华或成就,会受到社会的无形排挤。你很难在这里看到像埃隆·马斯克那样张扬的、个人英雄主义式的创业偶像。许多才华横溢的瑞典人因为受不了这种“枪打出头鸟”的氛围而选择移民去美国发展。但“詹代法则”在职场上却意外地催生了极度的扁平化。
既然大家谁也不比谁特别,那么老板的意见就不一定是绝对真理。瑞典公司里,等级观念极其淡薄。员工敢于直接挑战上司的观点,而不会被视为“刺头”。
宜家(IKEA)的“民主设计”理念就深受此影响:好的设计不应该只服务于富人,而应该以低廉的价格服务大众。

Credits: Simon Paulin/imagebank.sweden.se
这种文化鼓励了基层员工的创新能动性。当一个实习生也敢指出CEO思维盲区的时候,这家公司的纠错能力和创新潜力是巨大的。

中国创业者是幸运的,背靠一个14亿人口的统一大市场,很多企业只需深耕国内就能成为巨头。
瑞典创业者没有这个福气。瑞典国内市场太小了,只有1000万人口。如果你只做一个瑞典语的App,哪怕全瑞典人都下载,也撑不起一家大公司。这种“先天不足”,使得瑞典企业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被迫要“Born Global”(生而全球化)的。
Spotify如果只做瑞典音乐,根本付不起高昂的版权费,它必须撬动全球市场。
Skype从第一行代码开始,目标就是连接地球上任何两个角落的人。
H&M如果只卖给瑞典人,早就破产了。
瑞典人从小就被教育要看向窗外。他们的英语普及率极高,几乎每个人都能用流利的英语进行商务谈判。他们的产品在设计之初,就会考虑国际通用的交互逻辑和审美标准,而不是带有强烈地域特色的“土特产”。
当其他国家的企业还在艰难学习“出海”时,瑞典企业从成立那一刻就已经在“海里”游泳了。是生存压力,而非天生神力,逼出了他们的国际化能力。

如果把瑞典的成功全归结为文化,那就太天真了。瑞典政府在科技创新上的前瞻性布局,功不可没。最经典的案例是1998年推出的“家庭电脑改革”(Hem-PC reform)。
在那个电脑还是奢侈品的年代,瑞典政府出台政策:员工可以通过税前工资租赁电脑,几年后可以低价买断。这相当于政府变相补贴,让电脑以极低的成本进入了普通瑞典家庭。
Credits: Lieselotte van der Meijs/imagebank.sweden.se
这一政策直接催生了一代“极客少年”。
Spotify的创始人Daniel Ek、Minecraft的主创Markus Persson,都是在这个时期拥有了自己的第一台电脑。当别的国家孩子还在玩泥巴时,他们已经开始在地下室里没日没夜地自学编程了。
这种国家级的“数字基建”,不仅是铺光纤,更是普及设备和数字素养。它为瑞典后来的互联网爆发储备了全世界密度最高的各种早期开发者和精通技术的种子用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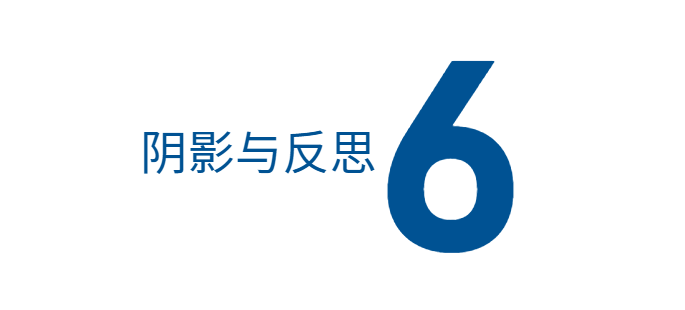
写到这里,如果还不提瑞典模式的问题,那就是不客观了。
的确,瑞典并非天堂,它的创新模式也正面临着严峻挑战。
虽然瑞典经济长期稳健,但在上世纪80-90年代曾经历低增长、高通胀、货币贬值、银行不稳定、政府债务飙升等严重危机。 瑞典通过引入公共支出上限、财政盈余目标、债务锚等制度改革,才得以恢复经济健康,但该历史也提醒:即便成熟经济体也存在结构性风险。
从绿色转型的角度,虽然瑞典大量使用可再生能源,且水电、生物质等资源丰富,但要使新技术(如波浪能)商业化仍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瑞典在“高消费、低排放”方面虽表现优异,然而要进一步推进完全可再生电力(目标2045年)和新兴清洁技术,还面临制度、经济、技术多重瓶颈。
另外,瑞典65岁以上人口比例较高,目前约20%,预计到2040年将升至约23%。随着人口寿命延长,医疗与养老服务需求持续上升, 不断增长的养老需求仍给社会福利系统带来压力。
最后是“不可复制性”。瑞典模式建立在人口少、高度同质化、且拥有深厚工业底蕴的基础上。那我们应该从瑞典模式中看到什么?
瑞典无法被复制,但可以被参考。
它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在于:
“效率”不仅仅只有“快”这一个维度。
我们习惯了用“时长”去衡量勤奋,用“速度”去衡量发展。但当我们想要从0到1创造出像Minecraft那样充满灵性与想象力的产品时,单纯靠“卷”时长是无效的。真正的颠覆性创新,需要的是“松弛感”。
这种松弛感不是懒惰,而是大脑在安全环境下的自由探索。是允许失败的底气,是跨界交流的闲暇,是敢于挑战权威的勇气。也许不是每一个国家都可以拥有瑞典的高福利,但至少可以在团队里试着建立一点“Fika时刻”,给紧绷的神经松一松绑。毕竟,绷得太紧的弓,虽然有力,但更容易折断。
从瑞典小镇走向世界:一家百年重工企业如何引领可持续发展?
细数瑞典那些低调到被人忘却,却又牛到令人发指的民族企业。